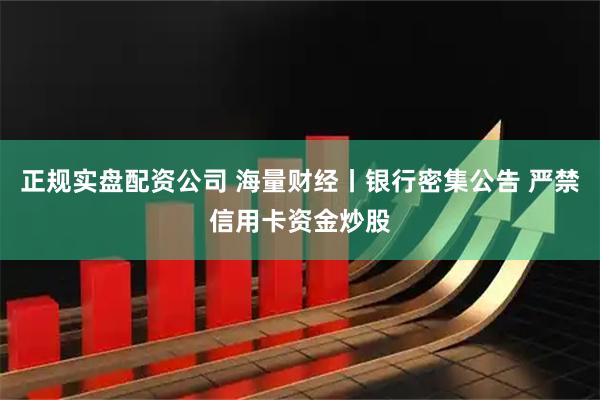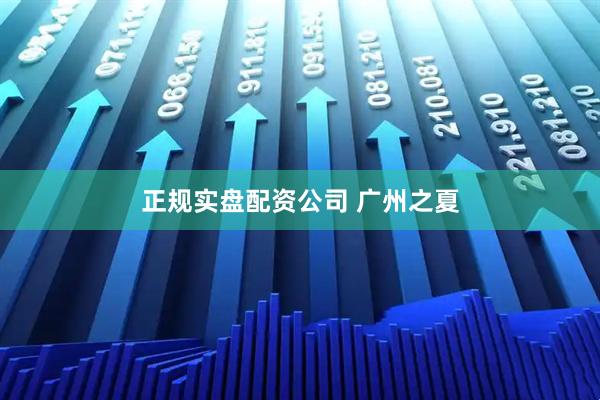
●林格量正规实盘配资公司
广州的夏,是腌渍青榄的咸,是木棉落到水面的轻,是骑楼砖缝里渗出的湿。
青石板上凝着夜雨,天一亮就化作白汽,像老茶壶嘴冒出的烟。我家窗台摆着外公留下的紫砂壶,他走后,这壶便不再泡茶。那日暴雨倾盆,檐溜水竟顺着壶嘴灌进去,注满了又从壶盖气孔淅沥而出。我忽然想起外公常说:“茶壶唔怕入水,最怕无茶。”如今壶肚空荡荡地映着云影,倒成了面照心的镜。
慢下来去看日子,细数一幕幕生活,惊觉每刻竟如此柔和。
东山三号车站榕树下打牌的老人们总喜欢把木凳搬到阴凉处,手里攥着一把蒲扇,却很少用力扇风。扇子摇出的风是碎的,和透过树叶的光斑一起落在发上,透出某种自然的从容与安乐。他们谈笑间剥着荔枝,一句“食得多,跌得快”,不知是说果子,还是人生。
新河浦邻居陈伯拎着生锈的洒水壶,壶嘴滴下的水珠落在苔藓上。他忽然停住,弯腰端详这片绿:“这算不算偷养分?”我愣了一下,他却先笑了:“植物也晓得夹缝里讨生活。”说完浇完花,哼着曲儿走了。后来我发现鱼池边的苔藓总比别处肥厚。原是围墙挡住了正午骄阳,雨又总把墙根打得湿润。直到前日暴雨,鱼池半边瓷砖被冲垮,露出植被交错的根。孩子们围着喊“烂了”,我却发现断裂处隐约冒出崭新绿意,忽然明白有些生长是看不见的。此刻,我蓦地想到童年。
巷子里,穿背心的阿伯推着自行车踱步,车筐里塞着两罐汽水,玻璃瓶身凝满水珠。他忽然停住,仰头盯着电线上停歇的麻雀。麻雀缩着脑袋,羽毛蓬松如旧棉絮,却在他靠近时扑棱棱飞走,留下一串啁啾。阿伯苦笑一声,从裤兜摸出打火机,点燃一根香烟。火光照亮他眼角的褶皱,那里面藏着无数个这样的夏夜——蚊虫、单车、飞走的雀儿,还有永远抓不住的某种痒意。
天字码头渡轮的马达声搅碎过无数星月,和江面的薄雾缠作一团。穿堂风裹挟着十三行旧址的檀香味,混着肠粉摊蒸笼掀开时的白雾。推车叫卖的豆腐花担子摇着铜铃,叮当声惊醒了趴在竹床打盹的老猫。天台上晾着的睡衣布料在风里轻轻拍着铁栏杆,似海鸥啄浪。这些被时光打磨着发亮的时刻,像极了广州人的性格——经得住“晒”,耐得住“浸”,在烟火气里生出独有的温润与从容。
这个城市的夏天从未真正开始或结束,它只是不断折叠自己。当第一滴秋雨落在遮阳棚上时,我会想起那个在士多店前数蚂蚁的下午。黑蚁队伍搬运着饼干屑穿越水泥裂缝,儿子问:“它们要搬去哪里?”我指着云层缝隙漏下的光斑说:“去夏天该去的地方。”
很多问题的答案,无非是藏在过往、此刻或未来。所谓永恒,不过是无数个五分钟的叠加——五分钟里,蒲扇摇出一阵风,车轮碾过一片落叶。当荔枝红透街角,当木棉絮落满长堤,总有人弯腰拾起些什么——或是掉落的钥匙,或是童年的蝉蜕。这些碎片互不相干,却又在某个恍惚的瞬间,化作回忆,日日永恒。
(作者系广州作家)正规实盘配资公司
炒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